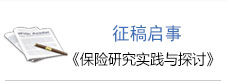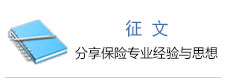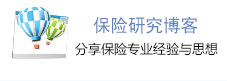链接:宪章橡树寿险衰落的中国启示(中国保险学会博客 :徐高林的个人空间)
重温阿姆斯特朗调查对我国保险业发展和监管的启示
——中美保险业跨世纪比较
杨明生
[摘要]我国当代保险市场与19世纪的美国保险市场有诸多相似之处,也逐渐出现了一些美国当年曾经出现过的问题。阿姆斯特朗调查促使美国保险业对自身存在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由此引发了美国保险监管的一次重大变革,对美国保险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经验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我国保险业应正视现阶段所凸现的各种问题,健全法规,正本清源;正确认识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把握保险本质,绝不偏离主业;增强竞争合作,实现竞争多赢。
[关键词]阿姆斯特朗调查;保险业发展;保险监管;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F84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306(2010)12-0003-07
一、阿姆斯特朗调查及其意义
在19世纪的美国,保险业高速发展,但保险市场也较为混乱。当时有不少寿险公司在推销人寿保单时误导宣传,忽视保单持有人的权益;采取割喉式的竞争模式,许诺投保人高额的佣金回扣;投资纪律松懈,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盛行;甚至动用巨资影响立法机关对保险业的立法。其间,也有很多人身保险公司由于管理不善而被迫宣布破产。对此,美国公众一直颇多微词。20世纪初,数个大型寿险公司相继爆出丑闻,更是激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不满。
鉴于上述问题的严重性,1905年纽约州成立了由参议员阿姆斯特朗(Armstrong)为首的委员会,开展对保险业的调查。1906年该委员会完成了调查,公布了著名的《阿姆斯特朗调查报告》。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许多人身保险公司的不合理现象被揭露出来,如公司办公费用浪费惊人;保单持有人利益被忽视;相互保险公司的保单持有人对公司事务根本无法控制;代理人的佣金和公司官员的薪水太高等等。纽约州议会根据这一报告通过了阿姆斯特朗法案,法案的主要内容有:
(1)所有大型相互制寿险公司重新进行董事选举;(2)禁止所有保险公司投资股票;(3)限制大型人寿保险公司规模,促进中小保险公司增长;(4)禁止保险公司进行政治性捐款,限制保险公司对立法的游说活动;(5)统一保险代理佣金水平,限制保险公司的营销费用水平;(6)禁止唐提式保单,确保保单持有人能每年获得分红;(7)寿险保单标准化;(8)强化保险公司的报告和信息披露义务;(9)严惩保单回扣等扰乱保险市场秩序的行为。
纽约州通过阿姆斯特朗法案后,各州均予仿效。纽约州对保险资金运用的从严监管,极大地保证了保险企业的财务稳定性,甚至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期间,纽约州也没有一家寿险公司破产。
阿姆斯特朗调查是美国乃至世界保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确立了保险专业化经营、保险资金运用管制等一系列现代保险发展的重要原则,强化了以保护保单持有人权益为核心目标的保险监管的地位和作用,影响极为深远。今天重温这一案例,对我们深刻认识当前中国的保险市场有重要的启示。
[作者简介]杨明生,现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二、中美保险市场跨世纪对比
19世纪的美国保险市场与我国当代保险市场,虽然间隔百年,但仔细比较,却有诸多相似之处。
(一)保险业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19世纪后半叶,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在世界所占的比重为17%,位居英国(36%)之后;到1890年这个数字改写为31%,超过英国(22%)上升到第一位,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1865年,美国铁路线长仅3.5万英里;1900年,全部铁路线长度达26万英里,超过欧洲铁路线总长度。这种发展速度和不断超越的感觉与当今中国非常相似。
在此背景下,美国保险业也出现了大发展。19世纪中期到晚期,经过30多年的发展,美国寿险业从当初的几家公司发展到1869年末的110家公司(见图1)。在纽约州经营的保险公司数量就由14家增加到了69家。在此期间,美国寿险业的认可资产从1860年的0.17亿美元迅速增长到1900年的17.42亿美元,接下来的10年更加迅猛,至1910年已经翻番,达到38.76亿美元(见图2)。
图1美国寿险公司数量变动统计(1860年~1910年)
资料来源:Frederick L. Hoffman, Fifty Years of American Life Insurance Progress,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11.
图2美国寿险业认可资产和公司数统计(1860年~1910年)

以当时规模较大的一家——宪章橡树保险公司(Charter Oak Life Insurance Company)为例,1863~1872年是其高速发展的时期。公司的代理人队伍非常精干,保证了公司的客户基础。1863年末,宪章橡树的有效保单3 047张、保额590万美元,公司总资产约为65.74万美元。在公司承保业务达到顶峰的1869年,一年之内公司销售的保单就超过7 200张、保额超过1 800万美元。到1875年该公司资产总额已经高达1 350万美元。1870年,纽约保险业监理专员指出,“寿险业已经成为美国最具商业利益的业务之一”。
可供参照的是,自2002年到2009年的7年间,我国保险公司数量从42家增加到131家,保费收入增长2.6倍达1.1万亿,保险公司总资产增长6倍多,达到4.8万亿,保险业资本金增加11倍超过4 000亿,保费收入跃居世界第7,比2000年上升9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因此相当一部分工商企业跃跃欲试想进入保险业。保险业成为投资者追逐的重点和热点。
(二)保险的社会认知度较低
尽管19世纪美国保险业增长强劲,但在当时许多批评家却公然谴责它是对生命的亵渎。他们认为保险把人们的生命变成了一件“商品”,并把死亡抚恤金视作“血腥钱”。人寿保险公司不得不大规模地进行广告宣传,以消除人们的这些观念。直到相当长时间以后,美国公众对保险公司产品的态度才逐渐由反对开始转为接受和支持。
当前中国民众对中国保险业的认知程度有待提高。恒安标准寿险认知指数显示人们对寿险本身接受度在逐步上升。但是,人们对寿险的财务规划能力及意识还远未成熟,中国人的“险商”仍不合格。目前我国购买保险的人数比例仍很低,对风险存“侥幸心理”是主要原因之一。调查显示,人们比较关心日常生活的消费,追逐较高的生活品质,但较少考虑未来的储备和财务规划。很多消费者虽然了解并认可寿险的作用,却没有购买行为。
(三)经营困境
19世纪美国保险公司破产率较高,有些公司成立目的明确,就是将寿险视为一个快速盈利模式,都想成立公司、快速盈利,这就导致很多公司无力履行对投保人的长期承诺。许多保险公司的经营者不仅不熟悉业务,而且创立动机不纯,要么一味跟风投机,要么沦为大股东资本运作的棋子。尤其是出现了各界名流纷纷在寿险公司董事会中挂名,却从不实际关注公司业务的怪现象。由于运气不好或者管理不善,恶果很快显现出来,在1873年爆发全面的经济危机之前,已经有30家寿险公司消失了。经济危机正式爆发以后,在遍布各行各业的倒闭潮中,寿险公司的崩溃持续加速。危机中破产的全美最大一家寿险公司是康涅狄格州的宪章橡树寿险公司,倒闭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失误,集中体现在三个投资规模上百万美元的项目上,致使不良资产超过了公司总资产的20%。
当前中国也有一些善意的企业家出资控股或参股保险公司,但经营目标似乎尚不明确,在业务规模、市场份额与经济效益之间摇摆不定。在“惟保单数量、保费规模”是图的价值导向下,许多保险公司仍是外延式发展方式占主导,一直没有摆脱对保费的崇拜,具有强烈的“数量扩张”冲动,很难说真正秉持了理性经营的原则。部分保险公司常年经营亏损,综合成本率连年高企,偿付能力不足,只能依靠股东持续增资维持生存。
(四)尴尬的社会形象
1848年美国一位保险公司经理说,“保险行业的名声正在逐渐恶化。公众需要的是安全的、可以让人高枕无忧的保险业务。因此,在保险行业能够提供此类保障之前,业务拓展和普遍繁荣是不会出现的。”
在我国,10年前社会公众对保险、银行和证券等金融行业普遍有些偏激言论。如今,针对银行、证券的基本不再有,但对保险的偏激言论还不少,保险业的尴尬社会形象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健康发展。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投保容易理赔难,保险不讲信誉,服务过程出现断层,投保前后两副面孔;二是误导现象较为突出。任意扩大险种的责任范围、不介绍责任免除和犹豫期的情况、阻止客户对保险标的如实告知、以回扣招揽客户,承诺高收益率或以此做演示、与银行定期存款同期的投资收益做不正当的比较等等;三是“五假”行为时有发生。假保费、假赔案、假利润、假账本、假报表等导致整个行业的信誉度降低;四是保险供应与消费需求脱节。同质的产品多,差异性、个性化的产品少,开发的产品卖不出去,需要的产品买不着,保险条款普遍冗长晦涩。据中国保监会对5 000名北京市民的调查显示,在不买保险的人群中,有30%的人是因为理赔难,20%的人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保险产品,中国景气监测中心曾经会同中央电视台对北京、上海、广州7 000多位有消费能力的居民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17.3%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我国保险公司诚信度差,76.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一般,仅有6.2%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国内保险公司的诚信度好①。
(五)混乱的市场竞争
19世纪后半期,美国保险代理人通常会向客户支付保费佣金“回扣”,且回扣比例不断攀升;恶意诋毁竞争对手时常出现;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户,诱导转保、销售误导等恶意竞争手段屡见不鲜。
在我国,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日益增多,保险
①唐逖,浅谈如何提高保险业的社会形象,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9,(6)。
市场秩序混乱。割喉式的高手续费和佣金竞争便是其中之一。在实际经营中,许多公司利用不入账、作假帐等违规手段支付代理手续费在同业中争揽业务。除此之外,不执行已在保险监管部门备案的商业保险合同条款费率、交强险不按照基础费率承保、宣传保险产品时有诈欺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夸大投资性保险产品收益、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不经投保人同意代签保险合同等)、阴阳保单、阴阳发票、撕单埋单、虚挂应收、虚假批退、通过中介机构虚开发票套取费用、虚列资金项目、虚列费用等造假行为亦屡禁不止。
(六)对保单持有人权益的侵害
19世纪的美国保险业存在许多损害保单持有人权益的现象,试举例如下:
诱导转保。19世纪美国人寿保险公司代理人经常诱使其他公司的客户退保,转而向自己所属的保险公司购买保单。由于这些保单往往已经投保多年,退保使得保单持有人损失惨重,引起了相关权益人的强烈愤慨。
唐提式保单。1868年,公平人寿在美国寿险市场上首先推出唐提式保险(tontine insurance)。在该保险中,保费的一部分用于购买普通终身寿险,余下的部分存入由保险公司管理的投资基金。属于保单持有人的投资收益和分红在保险期限内(通常是20年)都置于这个基金中不作分配。如果某一保单持有人在保险期间内死亡,受益人仅能得到指定死亡保险金(specified death benefit),而不能得到该基金的分红和盈余。全部的分红和盈余将于保单到期日在生存的保单持有人中进行分配。由于预期回报很高且能迎合人们的赌博心理,此类保单对投保人有很大的诱惑力。到20世纪初,唐提式保险已经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寿险产品。1905年,唐提式保险业务占到美国整个寿险业务量的2/3。唐提式保单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侵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果投保人在保单期间内死亡或未按时缴纳保费,就会丧失分红和投资收益的分配权,这是带有赌博性质的不公平条款;二是保险期间内不分红,这很容易导致红利被保险公司挪用或侵占。同时唐提式保单的高收益宣传也涉嫌欺诈,很多客户抱怨,从唐提式保单中获得的收益没有达到保险公司预估的回报率。
在中国当前的保险市场,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的行为也对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产生侵害,试举例如下:
1.假机构、假保单和假赔案等。利用保险产品进行诈骗已经成为保险业的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疾,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根据保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9年7月保监会决定开展打击保险业“三假”专项工作至2010年5月末,全行业共发现和查处各类假冒保险机构案件32起,各类假冒保单20余万份,各类虚假赔案超过1.6万件。全行业向公安机关移交并已立案侦查的“三假”案件达149起。
2.销售误导。主要表现为寿险产品销售过程中的不实宣传,绝大部分集中于投资理财型产品和银行邮政渠道。存单变保单的客户投诉时有发生。据中国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①,2009年,保监会收到的反映欺诈误导等不诚信问题的信访投诉件1 516件,占违法违规类信访投诉总量的32.37%,在各类违法违规信访投诉件中占比最大,并且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
3.理赔难。消费者普遍反应投保容易、索赔难。保险销售人员在销售产品时往往不愿向潜在的投保人披露不利的信息,在介绍产品的过程中,有些营销员把可获得的保险理赔说得“天花乱坠”,但却对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含含糊糊,造成消费者对索赔要求不明确,在实际理赔时发生困难。
(七)公司内控失灵
阿姆斯特朗调查报告显示,19世纪美国保险业高管在公司内行使权力不受任何限制,高管薪酬普遍较高,成为社会舆论议论谴责的焦点。美国公平人寿副总裁举办的一场化装舞会花费10万美金(按2000年物价水平折合200万美元),全部由公司负担;部分公司高管的仆人工资亦由公司支付;有的公司还用高于市价2倍以上的价格购买银行股票。公司内部控制虚设,法人治理混乱。
同样的现象在目前我国的保险市场上也有出现。以瑞福德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例,2008年12月15日,保监会稽查局根据举报和各方面报表反映,对存在严重问题的瑞福德实施综合检查。检查报告反映了瑞福德健康保险公司经营五方面的问题:1.隐瞒股东信息,骗取行政许可,严重违反法律;2.内控混乱,关联交易盛行;3.违规开展业务,财务数据虚假;4.投资决策管理混乱,损失巨大;5.准备金严重不足。保监会
①中国保监会2009年信访投诉统计数据。
审慎决策,认定瑞福德经营困境难以为继,果断处置要求更换股东单位,撤换董事长,并对一批高管予以行政警告。瑞福德案例在中国保险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中国保险业市场迄今为止、第一家被监管部门勒令重组和股权转让的公司,显示了监管者治理市场乱象的决心。
(八)灰色关联交易
阿姆斯特朗调查揭露,19世纪许多美国人寿保险公司都控制着信托公司,而保险公司董事往往兼任信托公司董事,并有权以成本价从信托公司购买证券。阿姆斯特朗调查认为,保险公司许多投资行为“削弱了公司官员的责任感,通过使用公司资金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管理人员和董事们的获利机会,并为了提高个体私利轻率的行使公司赋予管理人员的酌情权”。
在我国当前的保险市场上,部分保险公司通过复杂的股权架构,操控保险公司与关联企业进行交易,实施利益输送,并不按规定向监管机构报告。灰色的关联交易不仅会损害保险公司股东的权益,也可能对保单持有人的权益造成伤害。保险业如何规范关联交易行为,这既是监管者面临的挑战,也是整个保险行业亟需解决的课题。
三、对我国保险业发展和监管的启示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保险市场与19世纪美国保险市场非常相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真学习百年前美国保险业的治理经验,并对我国当前保险市场进行系统反思,必将有助于我国保险业的规范和发展。
(一)正视发展阶段,避免重蹈覆辙
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国保险业改革发展取得了明显成绩,发展形势很好。但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由于我国保险业起步晚、基础薄弱、覆盖面不宽,功能和作用发挥不充分,目前还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初始时期,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一是保险市场不成熟,保险市场体系不够健全,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市场秩序不够规范,服务水平有待提高;二是保险经营主体不成熟,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和低产出的“三高一低”现象较普遍,增长方式粗放,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三是保险监管者不成熟,我国保险监管机构设立时间不长,监管经验有待积累,监管制度有待完善,监管的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四是保险消费者不成熟,人民群众风险和保险意识不强,对保险了解程度不深,整个社会的诚信也有待提高。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首先,近期的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对我国保险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不是因为我们成熟,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与欧美保险市场同等的阶段。我国保险市场既有初级阶段的无序混乱,又蕴含金融混业等新兴的发展风险,因此我国的保险经营应当更加审慎,保险监管应当更为严格。培育市场可以加快,但不能超越所处的发展阶段。其次,我们应该正视当前保险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充分考虑初级阶段与成熟市场的发展差距,着重向同等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学习和借鉴,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当前成熟市场的做法,避免“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再次,我们应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和行政监管调控这两个手段的作用,一方面依靠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通过市场价格和消费者选择来充分调动市场资源,另一方面也要努力用好行政监管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以维护被保险人利益为核心,不断加强和改善监管,通过监管形成约束规范公司行为的“倒逼机制”,营造依法合规经营的环境,从而推进市场秩序的持续好转,确保市场安全、稳健运行。
(二)健全法规,正本清源
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是规范保险市场、保护保单持有人的根本手段。与美国相比,我国部门立法体制存在局限性。一味地将保险业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保险法》的不断修订,显然是不现实的。当前要充分发挥行政规章的作用,如对于《保险法》仅作原则性规定的问题,可以通过制定保险规章和实施细则来解决。对于保险法律适用中存在相对突出的、普遍性的问题,可以通过提请相关部门制定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来解决。
新《保险法》修订后,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仍有部分重要制度亟待研究制定,如保险营销体制、保险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保险业信息披露制度、保险社团与自律机构的地位和作用等。保险业界应当加强保险法律、法规的适用研究,促使各类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正确适用相关法律,并及时发现和总结在法律适用中比较普遍的、争议较大的现象以及新生的保险现象,及时与有关机构沟通,促进保险法制的相对完善。
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最大的缺陷是执行不力,法制观念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应以新《保险法》为基础,积极完善各类规章制度,保证新《保险法》的贯彻实施;完善监管执法制度和监管责任制度,进一步明确保险监管执法的具体适用程序和准则,探索建立一套明晰的监管责任制度;健全监管规章制度的定期清理机制和跟踪考评机制,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要加快有关金融混业的立法工作。在我国,金融混业已经是一个事实。形式多样的金融集团大量涌现,传统的分业监管体制曝露出很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金融集团将有可能利用规则漏洞进行监管套利,从而削弱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可借鉴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等的相关立法经验,如台湾地区的《金融控股公司法》(2001)、日本的《金融控股公司整备法》(1997)等,抓紧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控股公司法,设立防火墙、实施并表监管,促进相关监管部门互动配合。
(三)正确认识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
在阿姆斯特朗调查之前,纽约州政府也存在两种顾虑,一方面担心这种广泛深入的调查会损害保险业的公众形象,另一方面担心如果放任不管保险业会越来越乱。而阿姆斯特朗调查及其后续成果充分证明,有效的监管是促进被监管者持续健康发展的利器。阿姆斯特朗调查及整改措施恢复了美国公众对保险的信心,各州纷纷效仿。1904年阿姆斯特朗调查前,全美有106家寿险公司,而在1905年至1914年的十年中,就有288家寿险公司设立,出现了一个19世纪6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公司设立高潮。与此同时,美国寿险公司业绩明显增长。整个寿险业的有效保额从调查时的20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一战结束时的近460亿美元。
我们学习阿姆斯特朗调查的经验,就是要充分认识监管和发展的辩证关系,认识到严格有效的监管是保障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途径,并在此基础上扎扎实实做好监管工作。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1)监管要逆周期。在对近期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过程中,各国政府和监管部门普遍认为,应加强金融逆周期监管,从而有效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明确的是,逆周期监管不是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采取的阶段性措施,而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尤其是在景气阶段更应注重严格监管,以避免狂热的市场投机气氛累积风险。逆周期监管政策的实施应当持之以恒,不应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忽紧忽松。20世纪末美国颁布《金融现代化法案》,对金融业全面松绑,鼓励和推动金融创新,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立法者却对由此引发的投机和过度创新活动估计不足,金融衍生品交易泛滥且缺乏监管,最终酿成全球的危机,应当引以为戒。落实到中国市场,可以例举的是,近年来一些保险公司依赖发行次级债补充偿付能力,实现扩张经营,应当说这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容易在金融机构间引发系统性风险,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2)监管要遵循市场规律。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探索中国市场经济道路的历程。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和监管都必须植根于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原则,不能回到计划经济和行政指导的老路上去。具体的讲,《保险法》修改以后,保险业投资渠道全面放宽,保险产品投资利率已经市场化了;近期保险会计制度和准则修改以后,准备金评估利率实现了市场化,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也已经市场化了。那么下阶段我们就要逐步实现保险费率的市场化,让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也全面市场化。这实质上也是公平对待保险消费者、维护保单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客观要求。(3)监管应当着力在法人机构。这些年保险业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屡查屡犯、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保险法人机构的监管不足。法人机构是经营决策的核心,是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源头,而基层经营单位仅仅是执行机构。不从源头上予以查处并追究责任,势必导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下一步监管的重心应当锁定保险法人机构。
(四)把握保险本质,绝不偏离主业
保险发展到今天,其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深化和拓展。正确认识现代保险与传统保险的关系,关键是把握保险本质,既要继承和发挥传统优势,又要避免退回到传统狭窄的保险领域里去;既要发挥现代保险多功能、宽领域的优势,又要避免偏离保险主业。保险的本质是风险补偿,现代保险产品创新要注重以保险需求为中心,可以附带投资功能,但不能喧宾夺主,不能偏离主业。在资金运用方面,保险也与证券和银行有很大区别,应当体现保险资金运用特征,保持稳健,遵循安全性原则。
常言道,“术业有专攻”。金融系统三大支柱行业各有其特殊的功能和盈利模式。投资银行是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靠高杠杆率经营,追求高收益,偏好高风险,是一种“猎人文化”;商业银行是买卖货币、受授信用的特殊企业,主要依靠利差收入的盈利模式,受资本充足率约束,风险偏好趋中,是一种“农耕文化”;保险起源于相互制,是一种“一人为众、众人为一”的社会共济机制,依赖大数法则和精算原理,受偿付能力约束,主要靠承保获取利润,偏好低风险,是一种“互助文化”。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保险业凡没有偏离主业的机构都没有受到重创,凡是偏离主业的机构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如AIG就是令世界震惊的典型。
当前国内有关保险业的盈利模式问题存在争议。一些人坚持认为“以投资盈利弥补承保亏损”是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惯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在近一个时期,我国多数保险公司也确都以投资盈利来弥补承保亏损。但我们认为,这一现象并不是保险经营规律决定的,而是我国保险业发展模式粗放的体现。依赖投资的盈利模式实际放大了保险业所承担的风险。资本市场波澜诡谲,瞬息万变。要实现我国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强调承保和投资共同盈利,两个轮子协调运转。我国保险行业应当自觉抵御来自资本市场的诱惑,产险、寿险都必须要求承保利润,以防止因为资本市场振荡引发业绩巨幅波动。
根据新会计准则,保险公司的混合合同收入要经过拆分和重大风险测试以确定是否属于保费。从长远看,保险公司任何一种提供给消费者的保险产品都必须经过上述测试以确定其保险属性。不能通过测试的就不能算作保险产品,而是其他金融产品,此类产品应由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比如理财、证券类产品就应当由商业银行或证券公司经营。这类金融服务也应当接受其他监管部门的监管。如果保险公司有能力且有意愿经营其他金融产品,应当采取金融控股公司等综合经营的模式进行,接受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以避免监管真空和风险跨行业传递,酿成系统性金融灾难。
(五)增强竞争合作,实现竞争多赢
目前,割喉式竞争是困扰我国保险市场的一个难题。这种保险市场的非理性竞争呈现的是一种“纳什均衡”(非合作博弈)情景,似乎大家都处于“囚徒困境”的两难选择之中。欲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增强集体理性,冲破“纳什均衡”的困扰。
对此我们提倡行业内的竞争合作,因为根据纳什均衡理论,合作是最有效的“利己策略”。合作博弈(正和博弈)是“双赢博弈”,双方利益都得到增加,或者至少一方利益增加,而另一方不受损害。保险市场无序竞争甚至破坏性竞争的现实告诉我们,虽然“纳什均衡”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悖论,它有利于增强竞争理性,但它还不能替代“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根据孟德斯鸠“法的精神”理论,“看不见的手”可被视为蕴含着自然法的精神,不能促成反“纳什均衡”的合作博弈。我们应当看到,合作博弈靠竞争主体的理性自觉是难以做到的,即使一时做到了也难以持久。破解这一难题主要还应依靠“人为法”来约束,同时辅之以“行业自律”。所谓“人为法”,就是指法律和规章等外部监管,使竞争主体不敢“闯红灯”。此外,由于法规也不是万能的,因此还需要行业自律组织,促使市场主体形成公约,共同遵守市场纪律。需要指出的是,监管部门既要支持行业自律组织的活动,又要保持对其监管,特别是防范各市场主体通过非法的共谋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形成行业垄断,侵害消费者权益。
Abstract:The current insurance market in China shares some common features with the America insurance market in the 19th Century. It has also exhibited some problems which the latter had seen in its nascent development stage. The Armstrong Investigation has prompted the American insurance industry to seriously rethink on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as a result, triggered off a major transformation on its regulation with profound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American experiences are worth our careful reflection. China ′s insurance sector should squarely face its existing problems at the current stage, improve on its regulation, and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se problems. The industry should properly underst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gulatory body; remain steadfast with the essence of insurance and committed to its core insurance functions. It should also seek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to achieve multiple winwin results.
Key words:Armstrong Investig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nsurance regulation; development stage
[编辑:吕鹏博施敏]保险研究2010年第12期INSURANCE STUDIESNo.122010